【習作】只能緊牽著手繼續走下去
很明顯的,她失智了。她的眼神渙散,口語表達遲頓,走路平衡感略差。但似乎還認得出來她的老伴。
這是母親節前夕的下午。夫妻倆看起來六十多歲、也許近七十,丈夫看起來身體硬朗,帶著妻子著輕裝坐捷運。背著背包。好心乘客讓出一個座位,丈夫用手輕扶著妻子的手臂,示意她坐著。坐下時她還稍微重心不穩地跌坐在座位上。妻子失魂的表情有點嚇到隔壁座的乘客;想說什麼卻說不出口;右手遲緩地舉起,不明的意圖讓丈夫一直撥著她的肩膀,說:「沒事!沒事!」直到她對隔壁座的乘客說出:「你有怎樣嗎?嚇死我了…」隔壁座的乘客似乎鬆口氣,也回說:「沒事…沒事!」
丈夫把背包放下,讓妻子抱著,好讓他看一下捷運地圖。捷運到站。只聽見丈夫對妻子低聲咕噥:「走了…走了…」然後背上背包,捷運車廂門一開,他就牽著她的手,步出車廂,往手扶梯的方向走去。離手扶梯還有一段距離。他緊牽著她的手,眼神直視向前,並肩一起走著……
****
這對老夫妻已經搬到淡水大約三年了。丈夫退休前是在一家國內車廠擔任廠長,年輕時憑著優異的學歷與成績,儘管家境不好,仍能靠著公費留考,拿到出國留學深造的機會。那時候,他選擇了日本。在出國唸書前,他與在大學時代就交往在一起的女朋友、也就是現在的妻子,辦了簡單的婚禮,隨後就攜著簡單的行囊,負笈日本。那年是1967年。
1960年代的日本,經濟正急速發展,工程相關領域也跑在世界的前端。丈夫帶著妻子勇闖日本唸書,習得一身的理論與技藝,也承襲了日系工程界嚴謹和一絲不苟的脾氣。而妻子也謹守著作為「妻子」的身份,專心陪伴在他身旁。短短不到四年的時間,丈夫取得博士學位,隨即返國。回台灣後,進入國內某車廠工作,
一做就是將近40年。伴著台灣汽車產業的成長,也跟上台灣自力研發汽車的年代。1978年,生下長子,也是獨子。定居在忠孝東路三段的巷弄內。一住也是三十多年。
五年前,丈夫65歲屆齡退休,那時妻子63歲。好似可以安享退休晚年,但妻子健忘的毛病越來越嚴重。妻子65歲時被診斷出有輕度阿茲海默症,生活自理、言語表達仍尚屬正常,但「遺忘」的頻率則是越來越高。有時是忘了家裡的電話號碼、有時是忘了自己住在哪裡;然後是忘了兒子的出生日期、兒子的姓名,甚至是忘了身邊的丈夫是誰。一直到了某天,妻子在住家附近的巷弄間走失。丈夫報了警,騎著跟鄰居借來的機車,在忠孝東路三段的巷弄間穿梭尋找,終於在隔了幾條巷子的三角窗騎樓,找到她。
這是妻子第一次走失,也是最後一次走失。當時,兒子已經離家,丈夫獨自照顧失智的妻子。為了讓走失的意外降到最低,丈夫決定賣掉老房子,買了一戶位在淡水的華廈。
決定賣掉住了三十多年的老房子,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尤其是當新舊房屋都已簽約交屋後,深藏數十年的記憶,隨著整理、打包、搬遷,一股腦全都打翻。丈夫常常獨自一個人整理著書籍、相簿;撫摸著那台1978年生產的Canon A1相機,那是台為了記錄同樣是1978年誕生的兒子成長點滴,而特地標了一個會,透過日本友人購買的、具備電子快門、電子測光功能、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一台相機,但也只用在兒子剛出生成長的頭幾年。
妻子總是失了魂似的坐在沙發上,看著重播的韓國古裝劇。
淡水的這座社區,是擁有七百多戶的大型社區。社區有警衛駐守,警衛都認識這對出入總是緊牽著手的老夫妻。社區周邊有圍牆隔出社區界線,家中又設有緊急電鈴能與警衛室聯繫。夫妻倆就在這個社區裡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。外出總是兩點一線,要不是去淡水馬偕醫院回診,就是去五百公尺 外的頂好超市採買;大多時候都是在社區庭園裡散步,偶爾走到淡水河邊步道吹吹風。這個社區是丈夫感到最有安全感的範圍,不論妻子的身體狀況或病程如何變化,他不再冒著她走失的風險。
****
這對老夫妻的獨生子,今年37歲,未婚。三年前,在一次與父親的爭執後離家,離家當天是距離母親忘記他是誰的那天的兩週後,是母親第一次、也是唯一一次走失的那天的一週後,也是母親被確診為輕度阿茲海默症的那天的三天後。在兒子正式離家與父母斷絕聯絡之前的三十四年,他們三人住在忠孝東路三段巷弄內的老公寓。
兒子在離家的前兩年,在不顧父親的反對下,辭掉在一家中型企業擔任軟體工程師的工作。這份工作對他而言,是無間輪迴的地獄,而且是他的父親為他設下的地獄。他從國中、高中、一直到大學,學業成績皆不甚優秀;為了滿足父親的期待,他在高中選了自然組,並且在距離「名列前茅」很遠的排序中畢業;在大學念了資訊工程,雖說是一流的私校,但還是念了五年、差一丁點畢不了業;入了社會,則是蹲在一間規模要大不大、薪水要多不多、職場未來不甚清晰的公司,當一位「工程師」。在他父親的眼裡,這個兒子是不知道哪根筋不對勁,在一位家教嚴謹、紀律甚嚴的父親教導下,盡只有這等成就。
對兒子而言,他永遠不是父親眼中稱職的兒子,甚至在父親眼中,可能不存在這個兒子。而他當「工程師」的那些年,對父親而言,頂多只能算是個正當職業;若論及他想當一位「攝影師」,這對他父親而言,只是個餘興消遣的玩意。拿餘興消遣的玩意當職業,不僅沒出息、甚至會餓死人!但唯有母親,是以在父親眼中近乎縱容、溺愛、放任的態度,一如過往的三十多個年頭;似乎只有在母親的眼裡,他,才存在過。
剛開始拿起相機的前兩年,是辛苦的。他什麼都拍。用過去幾年工作中所存到的錢,買了一台Nikon數位單眼相機,拍風景、拍人像、拍新聞事件。一個新的工作領域,沒人脈、沒案源、也沒收入。為了能如此繼續走下去,也只能暫時接一些軟體工程師會做的事情來養活自己。而這樣職業不穩定的狀態,也一而再地被他父親嚴厲挑戰。無法避免的,是與父親無盡的爭執,以及母親無盡的包容。
離家那天,老公寓裡瀰漫著多重低迷的氣氛。媽媽失智了。媽媽前幾天走失了。一輩子被媽媽照顧得無微不至爸爸慌了。爸爸要求兒子,不要再任性,去找份工作,過正當生活!
「媽媽不記得我了!」
兒子抵擋不住父親的藐視,似乎他的存在從未「正當」過;更抵擋不住母親的失智,奪走了這世界唯一能證明他的存在的證據。兒子在當晚,帶著崩潰的情緒離開。此後,父親有他的手機號碼,但不知他住哪、也未有聯絡。這一年,是2012年。
****
2015年母親節前的週六凌晨,妻子因噩夢驚醒。丈夫也因為妻子的夢囈而醒來。妻子的失智毛病似乎因為睡眠不佳、精神不好,而稍有嚴重的傾向。醒來後,盡對著丈夫投以失魂般的眼神,詢問丈夫「你是誰?」「我在哪裡?」「我們結婚了?」「有一個兒子?」「他是誰?」「他在哪裡?」
「我怎麼都不記得了?」
這是妻子失智以來,「忘記」最多的一次。以往透過丈夫誘導、解釋,妻子總能回想起些什麼,也都還能隱約記得睡在她身旁的,是她的丈夫;兒子是紀實攝影師;這裡是淡水。這次,似乎不管用了!
於是丈夫拿出了一本本的相簿,指著一張張照片對妻子說:「這是妳兒子剛滿月的時候」、「這是妳兒子三歲的時候」、「這是妳兒子國小五年級的時候」、「這張照片是妳兒子在妳55歲生日時,幫妳拍的照片」、「這張是妳60歲生日時,幫妳拍的」、「還有這張,是妳兒子去年拍的,有得獎的喔!」
妻子看著一張張的照片,似乎想起些什麼。對著丈夫說:「那你在哪裡?」丈夫沒辦法回應什麼,此刻,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一連串的記憶裡缺席。但他沒有後悔、沒有嘆氣。
「那我們的兒子現在在哪裡?」妻子問。
丈夫說:「我們睡醒後去找他!」
****
丈夫一早就準備著早餐,督促著妻子完成起床後的一切生活事宜。兩人穿著休閒,丈夫背著背包,起身出發搭捷運。往松山煙廠。在捷運抵達國父紀念館站後,夫妻倆在捷運月台找張石椅稍做休息。丈夫拿起手機,毫無猶疑,撥了號碼,這個號碼是已經存在手機內已久,但已經三年多沒有撥出的號碼。只是對方沒接。丈夫在語音信箱留言。
留言內容簡短,大致是這樣的:我是你爸,帶你媽來看你在松煙的展覽。待會就到。
這天是兒子第一次舉辦攝影展,展出內容是他在過去兩年作為紀實攝影師的成果。2012年至2014年的台灣並不平靜。有反媒體壟斷的抗爭、有服貿學運、有苗栗大埔張藥師的土地抗爭,這位新銳紀實攝影師可說是無役不與。對他來說,他看見事件、他參與事件、他記錄事件、他告訴整個社會和世界這些事件的來龍去脈,他似乎就跟著這些事件的人、事、物一起存在過。簡單來說,他透過紀實攝影的歷程,他看到自己的存在。而這次的展覽,只是讓他的存在更為確立、更為具有價值、甚至是更為正當。
他收到手機留言。他有點不知所措。站在展場入口處的角落,暗暗地觀察每一位入場的觀眾。他看到了他的父親、母親。父親的表情依然嚴肅,身形略為消瘦,看起來尚屬硬朗;父親緊牽著母親的手,四處張望;母親則仍如他三年前離家前所瞥到的,失魂的雙眼呆視著。
他心裡好害怕。
儘管在紀實攝影的領域裡,他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位置,內心更感受到自己存在於世的意義,但面對自己的原生家庭,他的思緒頓時墮入「存在感」質疑中。
「我是誰?」
「我存在於他們的世界嗎?」
以及「她不記得我了!而我,還存在嗎?」
這麼多年來,每當他在存在與不存在間掙扎時,他總是感受到一股暗黑空間的降臨。儘管他感受得到自己的思緒、感受到自己實體的肉身,但滿身的負面能量,總是把自己鑽往「不存在」的結論裡。
於是,他取消了展覽的開幕式。離開了展場、回到自己的工作室。回到屬於自己、讓自己最有存在感的空間範圍。
而他的父親母親撲了空。丈夫仍牽著妻子的手,走完展場,看完每一張相片。此時,作為父親,內心一股驕傲閃過,但那力道仍不敵失落。夫妻倆在松煙的戶外角落稍事歇息後,起身搭乘捷運返回淡水。
對妻子而言,為什麼要去松煙、為什麼要逛完展場一圈、為什麼要看完每一幅相片,已經不需要再透過引導、解釋、給予正確答案!此行原先的目的,已經不重要了!
對丈夫而言,儘管無法理解為什麼他們會撲空、為什麼兒子沒有出現,他無法、也無力責怪、憤怒,因為丈夫的內心,也墮入了暗黑世界。他在妻子失魂的眼神中,已經找不到自己存在的證據。
「我們都不存在」,是父子間僅存的共同點。
捷運人潮很多,車廂內滿是願意讓座給長者的乘客。夫妻倆在捷運上總是遇到善心的乘客,願意給予協助。只是乘客們看到妻子不穩的手腳、失魂的眼神,也都忍不住多瞄了兩眼。丈夫對於這些眼神,一直處於難以自處和適應的階段。但不管如何,忍過那不到一小時的車程,他們就能回到讓自己最感安全的地方。
捷運到站。離手扶梯還有一段距離。他緊牽著她的手,堅毅的眼神只能直視向前,並肩一起走著……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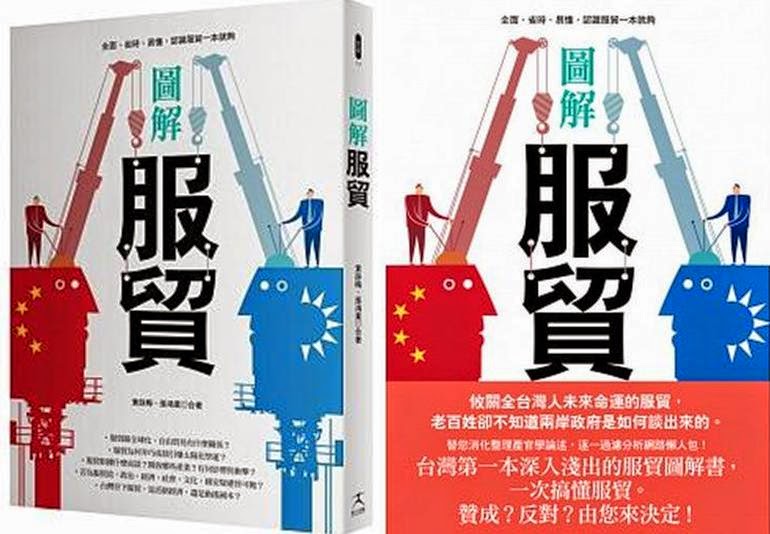


有潛力發展成中篇小說!
回覆刪除謝謝你…工作之餘、有靈感之時,我也會想持續擴充這個故事
刪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