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習作】佟振保
篇名:佟振保
作者:孫鴻業
備註:改寫自張愛玲<紅玫瑰與白玫瑰>,斜體字部分即引用原文。場景引自電影版<色戒>。
修改:1st 版
振保的生命裡有兩個女人,一個是他的白玫瑰,一個是他的紅玫瑰。一個是聖潔的妻,一個是熱烈的情婦。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。娶了紅玫瑰,久而久之,紅的變了牆上的一抹蚊子血,白的還是「床前明月光」;娶了白玫瑰,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飯黏子,紅的卻是心口上的一顆硃砂痣。
「這時局這麼不好,我們還約在凱司令!」鴻業興奮地對振保說道:「料得振保兄學成歸國,應在外商公司覓得一官半職,前途無量,大有可為啊!」振保聽了一陣誇讚,亦不由自主地感到自信了起來,提高聲調回應:「言過其實了,這幾年負笈海外,著實辛苦,如今學成,總算是不負家母期待。」振保能出國唸書,算是傾家族之資源,儘管佟家只是個小康之家,在鄉里間亦算書香門第,家教良好,振保能不負眾望,算是光耀門楣,「若能最國家,為社會做點有用的事,才算是不負栽培啊!」振保說的義奮感慨。
坐在凱司令咖啡廳靠窗的座位,店內僅有四組客人,櫃臺電話的鈴響聲大於客人稀落的談話聲。侍者眼光銳利地看著店內的客人,緩慢而仔細地掃瞄著,似乎是唯恐怠慢了,但又似乎是熟悉客人的所有一切。振保望著窗外,刺眼的陽光逼使著振保不得不瞇著眼,彷彿是想要與正午的日光挑戰,看清逆光中的窗外的景色。振保回過頭來,對侍者使了個眼色,交付侍者:「Coffee for two, please.」隨之對鴻業說:「今天我請客!」此時,侍者整理了桌面,收拾了菜單。當鴻業報以微笑並回說:「真是賺到了,恭敬不如從命囉。」侍者則投以銳利且致意的眼神。
鴻業撇見振保眼神中一股毫不經心,馬上換了話題問:「找到落腳的地方了嗎?還是要回到江灣和佟媽同住?」振保回神:「會住在士洪那,士洪那的大公寓,租了兩間房,我和篤保已經入住了。」士洪、振保與鴻業是相識多年的友人,家事背景的差異雖無妨三人的友誼,在人生不同的際遇,卻也在三人內心裡,有著羨慕、嫉妒、甚至是相互較勁的仇視。士洪出生在富貴人家,在振保的眼中,士洪的人生是再順遂不過的,與振保的一切都要白手起家向前衝相比,士洪所擁有的,著實讓他嫉妒;對鴻業來說,沒有良好的出生,也沒有放洋吃過洋墨水,士洪相形算是紈絝子弟,而振保儘管有著萬丈高樓平地起的衝勁,卻只不過是眼高於頂的執拗且不經世事的理想主義份子。鴻業不止一次地對著振保明嘲暗諷,一個人不可能順意地擁有一切,人生,得到些什麼,就必須失去些什麼,這是種交易!或許這對鴻業對人生的不如意的一種自我解嘲,但,尚未擁有什麼是他的優勢,因此也無須害怕失去些什麼,反而是開始期待即將能擁有些什麼。
「那你一定見過士洪的嬌妻囉?」鴻業詢問的語氣透著不尋常的弦外之音。「前幾天在福開森路閒逛,遠遠地見到她,親密地挽著另一個男人的手…。」鴻業的話只講到一半,振保帶著一抹斥責的微笑說:「你這樣夠囉,說三道四的,不怕被打下拔舌地獄?」振保的斥責讓鴻業發窘,並且振保繼續以維護的口吻駁斥:「嬌蕊大抵是不出門的,你應是認錯人了吧!」鴻業只翹起左邊的嘴角,露出一抹質疑的微笑,帶點不客氣卻似乎得到解答的語氣低語:「原來士洪他老婆叫嬌蕊啊,之前和他倆口子吃飯,還以為她只有個洋名,那個叫做什麼的….」振保瞬即回說:「王嬌蕊,他叫王嬌蕊,大抵是用士洪的姓起的名。」
* * * *
「篤保啊,怎會想找我出來呢?」篤保約了鴻業到舊書攤逛逛,篤保開朗又促狎地回應:「振保說,可以到舊書攤走走,買些學習用書,想說鴻業大哥熟門熟路,請您協助囉。」篤保是佟家的么子,受到振保和家人的溺愛,雖然家庭無法以栽培振保的方式,送篤保出國唸書,但振保卻想以自己的力量,以及未來在外商圈深耕的人脈,協助篤保未來的事業。「你講話真甜,難怪佟媽和振保這麼疼你。」鴻業領著篤保,跨越街廓,遁入巷弄,走入一間門面老舊的兩層樓傳統中式木造建築。店面無人照應,鴻業繞過層疊如人高的舊書,往店後走去,喊了一聲:「鄺老闆,老孫來買書囉!」鄺老闆這才露臉迎接,面色灰白倉促,有如方才做了虧心事。鄺老闆揚起他混有廣東話和內地不知道哪一省方言的腔音迎接:「老孫啊,好久不見,這次想找什麼書啊?」在鄺老闆企圖將鴻業帶回店面時,店後一名身著藏青素色旗袍的年輕女子,匆匆走上二樓。
「幫我好朋友的弟弟找些書,大抵是工程用書。」鴻業對鄺老闆解釋,隨即轉身對篤保說:「鄺老闆先前在港大唸書,青年才俊,學識涵養豐富,以後有什麼求學問的事,都可以請教他。」篤保笑笑地,在成山的書堆中找尋他所需要的書籍,鄺老闆也領著篤保,告訴篤保他的獨特圖書分類法,而木造的二層樓板滋滋作響,彷彿有十數隻鼠輩集結,不時擾人耽溺於書卷中的興致。
「這巷弄真美,氣質不輸老北京的胡同啊!」篤保買完了書,與鴻業一同步出鄺老闆的舊書攤,鴻業似有若無地感嘆者。篤保說:「是啊,鴻業大哥這麼喜歡古樸的建築,改天一同回江灣老家,有另一番景致唷。」篤保的回應似乎過於熱烈且不切心意,鴻業馬上轉了個彎、起了另一個話題:「你們住士洪家如何?」篤保回道:「還不錯,士洪大哥十分照顧我們,大嫂也很親切,最近士洪大哥遠賦英國。」篤保的言語突然遲疑了起來,鴻業有著不尋常的揣測,順著篤保的言語謹慎地發問:「士洪去英國啦?那家中少個男主人,氣氛就少一分熱烈了。」鴻業的語氣聽似惋惜,確有讓人莫名地感受到想深究的意圖。篤保的回應突然變得支吾且猶疑,不如慣常的順暢:「也不是熱烈不熱烈的問題,而是有幾次回去,不小心撞見振保與大嫂共處一室,」篤保的話說到此,語氣變得更緩慢而猶豫了,鴻業則聽似不經意地追問:「怎麼啦?什麼事讓你疑惑?」篤保大笑地回道:「沒什麼吧,只是聽到有趣的對話。」「對話?」鴻業挑眉地問:「有趣的?」篤保說:「對啊!大嫂說:『我有那麼甜嗎?』大哥回:『不知道—沒嚐過。』就這樣而已。」篤保和鴻業相望大笑,篤保的笑聲是單純、篤定而明亮,但鴻業的笑聲卻是帶著虛應與懷疑。
* * * *
「怎麼會突然想要來江灣?」振保對著鴻業問道。鴻業東張西望且虛應地回道:「上次篤保建議我可以來江灣走走,享受與上海城不同的古樸美景。」鴻業仍邊走路邊四處張望地回應道:「剛好這次你約我出來,那就來江灣走走吧,小橋流水,極簡的民居,順便探望一下佟媽,好久沒見到她了。」振保與鴻業走在一段石砌的小拱橋上,只聽見後方有叩叩叩的走路聲,趕路似地急於想超越振保與鴻業。鴻業放慢腳步,撇著頭打量了這個人的背影,穿著入時,靓藍色的旗袍上,鑲繡著靛藍色的大花,並點綴的紅色碎花,腳穿粗跟包鞋,走路的姿態些許生澀,似乎是不習慣穿高跟鞋,拿著小包,梳個包頭,鴻業說:「富貴人家的穿著,但走起路來卻不怎麼富貴。」振保僅瞄了一眼,眼神即處於放空的狀態,若有所思。
鴻業見振保雙唇微抿,眼神憂鬱,問道:「怎麼啦?今天是想找我談什麼事啊?我們邊逛邊談吧。」振保仰了仰頭,呼了一口大氣,才說道:「我想我愛上嬌蕊了。」振保講完這句話,言語即停頓下來,但卻加速他的步伐,雙手抱頭的模樣,似乎表示出不太想繼續談這件事,但鴻業卻以早已預料到的鎮定口吻追問:「怎麼回事?說出來會好一些。」鴻業有點氣喘地補充:「我們都老了,別走這麼快,就橋邊坐下談吧。」鴻業找了個橋邊路衝的位置,一個可以多方觀賞江灣景致的位置。
振保從他第一次見到嬌蕊談起,說到他們許多對話,斷斷續續、斷斷續續地:「『我頂喜歡犯法的。你不贊成犯法嗎?』嬌蕊說,『你知道我為什麼支使你?要是我自己,也許一下子意志堅強起來,塌得極薄極薄。可是你,我知道你不好意思給我塌得太少的!』嬌蕊又說過:『男子美不得。男人比女人還要禁不起慣。』還說:『你別說人家,你自己也是被慣壞了的。』又說:『也許,你倒是剛剛相反,你處處剋扣你自己,其實你同我一樣是一個貪玩好吃的人。』嬌蕊還說過:『我就喜歡在忙人手中裡如狼似虎地搶下一點時間來—你說這是不是犯賤?』再說:『其實也無所謂,我的心是一所公寓房子。』」
鴻業聽得一頭霧水,但好像也聽出一些端倪,直接問:「那你都說了些什麼?」振保無辜地回道:「應該都回『嗯』、『啊』之類的吧。」振保回得心虛,也回得不甚篤定。但鴻業不死心地追問:「就你剛說,嬌蕊說她的心是一所公寓房子,這段對話你們說了些什麼,給我說仔細點!」振保無辜的眼神,以也沒說些什麼語氣回答:
嬌蕊笑道:「其實也無所謂,我的心是一所公寓房子。」振保笑道:「那可有空的房間招租呢?」嬌蕊卻不答應了。振保道:「可是我住不慣公寓房子。我要住單幢的。」嬌蕊哼了一聲道:「看你有本事拆了重蓋!」振保又重重的踢了她的椅子一下道:「瞧我的罷!」嬌蕊拿開臉上的手,睜大眼睛看著他道:「你倒也會說兩句俏皮話!」振保笑道:「看見了妳,不俏皮也俏皮了。」
鴻業做噁且挑眉地笑道:「讀書人,你們共處一個屋簷下,該不會每天都在說這些挑情的話吧?」振保不回答,似乎也默認了。鴻業追問道:「該不會,你們挑情挑到心裡去了?」鴻業雖然早有預料到會有這樣的狀況,但卻也到抽一口氣地表現出驚訝的眼神,又追問道:「兄弟,睡了嗎?」振保又不回答,臉色凝重,眼神飄忽。這下換鴻業感到沈重,說道:「這你要我們怎麼面對士洪啊?」又追問道:「還有誰知道這件事?」士洪輕緩地嘆了口氣說:「沒人了,但嬌蕊好像寫信去英國,跟士洪要求離婚!」鴻業雙手僅捉住振保的雙肩,稍帶激動的手勢,急促的一口氣從鼻中呼出,然後平穩地說道:「兄弟,不是我不挺你,你這下英名難保。你曾說你想要的是單純的生活,學成歸國後想貢獻社會、貢獻國家,這下,嘖嘖嘖……」鴻業繼續說道:「你這是圖她的什麼,真是愛她的靈魂,或是愛上挑逗的刺激快感?」鴻業突然轉換了口氣,嘲諷地喫笑道:「你離開英國前,能這麼斷然地離開你口中懷念讚賞不已的前女友,卻陷落在跟嬌蕊的婚外情,你可能真是喜歡在家為良妻、在床為蕩婦的女人吧。」振保依然不作聲色,鴻業則拍拍他的肩膀說道:「這事你好自為之吧。走吧,天色晚了,我們快回去探望佟媽吧!」
佟媽家傍著小河,夏日夕陽垂柳,美景伴著一股濕氣,空氣中不時飄忽過一陣焚燒紙張的氣息。木造的房舍,已有點漆黑斑駁,看得出來是幢老房。佟媽算是有開點眼界的上海婦女,能送振保放洋深造,算是她最現代化的一部份,但傳統守舊的,還是他那一手家常菜飯、鯽魚冷盤、以及他那叨念的極致功夫。鴻業在佟媽家中、前庭、後院四處閒散張望,美景、佳餚、佐有點年份的黃酒,對鴻業來說,此刻是一切美好。振保則面對佟媽的嘮叨,一副逆來順受的樣子,讓鴻業看了發噱。當佟媽提起要為振保作媒,振保似乎也接受了。日月交替的暮色,提醒振保和鴻業該離開了,此時隔鄰傳來女子歇斯底里的呼喊聲:「他不只要鑽入我的身體、還要鑽入我的心。」鴻業挖苦地對振保說:「看來挑情挑到心裡去的困擾,不只你有啊!」
* * * *
「又約凱司令!這次換我請客!」鴻業對振保說道。振保臉色憔悴,身形是發胖了不少,藉口在外花天酒地,是眾友間不止聽聞且目睹的,這大概也是振保發胖的主因吧。振保自從逃離士洪的公寓、斬斷與嬌蕊的聯繫、與媒妁對象結婚後,行屍走肉。對婚姻不滿、對篤保不成材的不滿、對公司的不滿、對社會局勢的不滿、對一切一切都不滿,振保變得憤世嫉俗,讓人感到不如以往的親和善意。但眾友還是覺得他是幸運的,畢竟在這不佳的時局中,他所待的那家外商公司,外籍主管即將離開中國,佟振保即將接替,升任為佟副理!
「今天的凱司令感覺更冷清了,只有兩組客人。」鴻業隨口提到,又道:「振保,你剛過來的時候,有覺得外面的人,眼神都怪怪的嗎?」振保又是陣沈默。此時餐廳櫃臺的電話聲響起,只見另外一組唯一的女性客人拿起電話,講著廣東話說著:「二哥、二哥…」。振保持續沈默,沈默的空氣讓鴻業有點焦躁不悅。這次,鴻業和振保坐在靠內側、遠離落地窗的位置,室內光線昏暗,與室外的高度明亮,讓人的視覺感到不舒適,而振保依然期待用他的雙眼,看穿窗外。鴻業又試圖起了個話題:「那桌女客人穿著貴氣,靓藍色的旗袍,身材挺不錯的,看起來有點眼熟。」振保持續沈默,鴻業只好再繼續說道:「你瞧,她的咖啡杯口還留著唇印,肯定是你愛的那種良妻、蕩婦。要不要過去搭訕一下?」鴻業想以激怒振保、讓振保開口說話的企圖,再次徒勞。咖啡廳裡的唯一女性離開了,整間凱司令只剩下振保與鴻業,兩人偶爾眼神交錯,但大多時候,兩人共同望向窗外,鴻業不斷地抖著腳,試圖掩飾他的焦躁,儘管焦躁,但他的眼神依然專注。而振保,兩眼失神,儘管望著窗外,卻毫無目的,似乎是想看清現狀,但再亮的光線,他永遠是處在陰影的角落,振保永遠在夜盲中胡奔亂竄。
頓時,窗外出現一陣騷動,汽車突然急轉的煞車巨響,吸引了振保與鴻業的目光。隔鄰有一名男子從珠寶店衝出,飛身跳入車中,汽車瞬時疾駛而去。鴻業轉頭對振保急忙說道:「既然你不想講話,那我有事先走了!」
* *
幾小時後,鴻業走在福開森路上,迎面一台黑頭轎車駛來,駕駛座搖下窗戶,是振保,對鴻業說:「上車吧,出去兜風走走!」鴻業上車後不可置信地問振保:「你怎知道我在這裡啊?」振保漠然地回道:「你說你最愛在福開森路閒晃,就來這找你!」說畢,振保又沈默了起來。途間,只覺離上海城越來越遠,突然房舍變少,突然樹林增加,突然又是荒土一片。振保語氣低迷地說道:「時局不好,我們公司在內地有業務,我可以幫你安排。」鴻業右望著窗外的景色變化,只說了聲:「謝謝。」
振保一路開往上海郊區的一座礦場,天色已暗,鴻業拿出口袋中的懷錶,已是晚間九時許。當振保找定一處停車後,潸然淚下,雙手緊握著方向盤,低頭啜泣不能自己。鴻業拍拍振保的右肩,說道:「我都知道了。」當嬌蕊跟士洪提離婚的時候,士洪有拍份電報給鴻業,表達出他的痛苦與不解,但他也願意給嬌蕊自由。士洪甚至也猜測到是誰把他的老婆勾走,甚至願意給予祝福!「想不到你卻逃離了。」鴻業繼續說道。振保抽搐地接著說:「前幾天,在電車上遇到了嬌蕊,她胖了、老了、憔悴了、結婚了、有小孩了。」振保繼續說著他遇到嬌蕊時的情景:「我問她好不好?」嬌蕊笑了一聲道:「我不過是往前闖,碰到什麼是什麼。」嬌蕊繼續說道:「是的,年紀輕,長得好看的時候,大約無論到社會上去做什麼事,碰到的總是男人。可是到後來,除了男人之外總還有別的……總還有別的……」
鴻業不待振保說完,即刻插話:「有件事,我是對不住你的!」在振保搬離士洪和嬌蕊的處所後,嬌蕊找了鴻業,談了許久,期望鴻業能幫忙,挽回振保,嬌蕊那時還對鴻業說:「振保離了,我是不行的…」鴻業對著嬌蕊,露出無能為力的模樣。鴻業繼續對振保說道:「我不知道該怎麼幫你們,你逃了,而躲進另一個人的懷抱,幫了嬌蕊,幫了你,又會是讓另一個女人受傷。」鴻業嘆了一口長氣,語調低迷:「或許我怎麼做都是錯,因為另一個女人還是受傷了!」頓時,鴻業的臉色慌張的起來,揚起聲調、語氣些許地不平穩的繼續說道:「此時此刻,」鴻業倒抽了一口氣繼續說著:「正有人為了他們的愛情,負生的責任、負死的責任。振保,你何其幸運,你大可像逃離嬌蕊般地逃離現在的婚姻,也可以花費數十倍百倍於毀滅現在婚姻的力氣,做出挽回、補救。這都是你該負的生的責任啊!」語畢,鴻業以幾近冷酷的地,望著前方急促道:「我們快走吧,這裡是丁默邨的刑場。」再以幾近憤怒的聲調命令振保:「快走!」
振保在驚嚇中,催促著油門,加速離開這片荒土。迎面而來的,是四名士兵,各拿一隻手電筒往車中探照,振保踩了煞車,嚇直了的眼神,嘴唇顫抖不敢發任何一語,只見鴻業拿出一張白紙,通行證,振保慌亂不定地瞄到丁的親簽。鴻業低下頭,把通行證遞給士兵,並以銳利的眼神望向士兵,然後命令道:「讓我們過去!」振保再次催促著油門,從照後鏡撇見敬禮的士兵和自己淚眼未乾且恐懼無知的表情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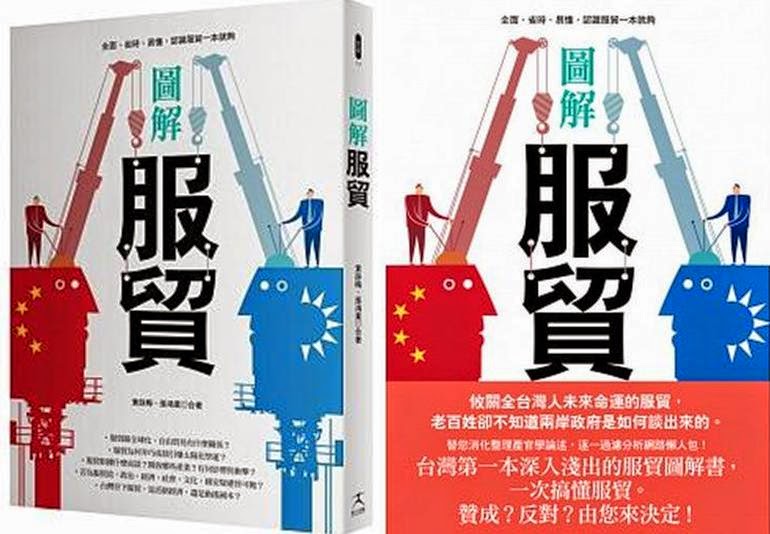


留言
發佈留言